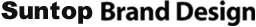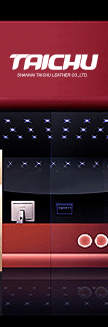自壁毯浅议标志设计重要性
标志设计从开始发展至今,一路走来越发让人们感受到了它的重要性,壁毯运动不也是这样.每一种事物都有其所代表的标志,壁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是一种标志设计.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欧洲壁毯工厂不停地复织古代的、特别是18世纪的壁毯.工艺师根据画稿,在织机上依画而织,画作的色彩、调子均需依样还原,制作工艺繁杂.因此,复制传统壁毯,织制成本颇高.传统的制作体系俨然与20世纪的社会脱节了,壁毯制作业一一这一古老的欧洲制作产业濒临衰落.
艺术家们希望冲破传统思想体制的束缚,愿意在传统的艺术与手工艺领域开始新的尝试.让·吕尔萨(Jean Lurcat)便是这其中的先驱,他对建筑空间和现代墙饰的兴趣,使他自光投向了昔日辉煌的法国壁毯业.
1939年,现代壁毯艺术的重要奠基人一一让·吕尔萨与画家图桑·杜布瑞(Toussaint Dubreuil)和马塞尔·高麦里(Marcel Gromaire)来到法国古城奥比松一一这个自16世纪以来以壁毯编织业为主的小镇,开始新的壁毯语言探索,决心重振法国标志设计壁毯业.
在让·吕尔萨的影响下,许多艺术家都积极参与到这场奥比松的壁毯复兴运动中.那些名字也都曾在这段鲜活的历史中留下印记.
作为这场复兴运动中坚力量的吕尔萨,在制作上,他开始与传统的精密复制绘画式的壁挂艺术决裂,充分发挥壁挂编织在艺术语言上的个性,并倡导不断开发织物纤维的新材料、新技法、新语言.他这一时期的壁挂创作注重壁挂艺术自身语言的挖掘以及构成形式上的变化追求.正是他在语言上的探索和建立的新范式,为“壁毯”向“纤维艺术”的转向建立了基础.此后,他在60年代所创立的“洛桑国际壁毯艺术双年展”上所激发的纤维艺术革命一一新璧毯运动,正是在这场奥比松复兴中汲取了营养.
“新壁毯运动”标志设计摆脱了具象绘画的束缚,推崇更接近抽象绘画和雕塑艺术的形式,壁毯变得柔软、便于移动,并且与环境相互呼应.可以说,该运动前所末有地接纳了壁毯媒介的物质特性.除了毛线、丝线或棉线,艺术家们不断尝试新材料,与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中国艺术家在这场现代艺术运动中的标志设计建构作用.1957年,让·吕尔萨曾来到北京举办个展.当时留学北京的保加利亚年轻艺术家万曼被其作品深深的感染,其艺术创作思路受到极大的冲击.70年代,万曼任教于浙美(现中国美院),在浙美创立了中国唯一的壁挂艺术研究所,成为推动中国纤维艺术发展的重要人物,培养了大批中国纤维艺术家.
万曼作为“新壁毯运动”的积极建构者,善于从中国传统“织毯”中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关联,以东方的视角反观西方现代艺术,为东方提供平等的对话立场.他的学生们在80年代与老师万曼一起踏上了“瑞士洛桑国际壁毯艺术双年展”的舞台,中国艺术家开始在全球艺术视域中崭露头角,给当今艺术史叙事的全球视角提供了标志设计积极建树.
纤维艺术与语言转向
“新壁毯”开始之后,古老的“壁毯”在当代实际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艺术门类一一纤维艺术,让·吕尔萨与他的“洛桑双年展”让壁毯的制作材料一一纺织纤维独立跳脱出来.纤维,成为一种艺术表达工具,通过“编织”来表达话语.从这种意义上讲,纤维艺术是与“洛桑双年展”伴生的.
艺术形态标志设计的多元化,风格的多样性,材料的综合性等这些诸多因素,构成了纤维艺术的现代性特征.它在本质上突破了传统艺术形式中一一材料处于隶属地位的观念束缚,促使了艺术家对纤维艺术在观念和形式上更积极的追问,也促使了艺术家们对纤维艺术独特语言更进一步的探索和大胆的实验.
纤维艺术标志设计作品借由其材料认识的反传统,走在了艺术的前沿领域,开始更多的趋向“实验性”,在艺术表现方面体现更多的“先锋性”,成为一种艺术的变革.波兰著名艺术家玛格达莲娜·阿巴康诺维兹,是这场现代艺术变革中旗帜性的人物,1969年6月在第四届洛桑璧挂双年展上,她创作的大型立体壁挂《红色阿巴康》横空出世,恩挂在洛桑州立博物馆的大厅,揭开了壁挂艺术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页,展示了壁挂艺术在创造形态上的重大突破,作品由平面的形式发展成立体的造型,进而成为三度空间的装置艺术.
后现代的“观念”意识越来越多地成为纤维艺术创作的“话语”,纤维艺术朝着“观念”与“装置”艺术发展的倾向越案越鲜明.某些东西悄悄隐匿和潜伏在这些作品中,人们试着去表达,试着去揭露,“纤维”与“编织”被赋予新的含义,“新壁毯”,未曾止息,它通过“语言的转向”得到新的延续.相信北京标志设计也会永不止息,在通过某一种的介质而得到更上一层楼.